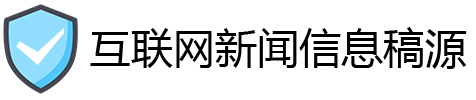團(tuán)結(jié)報(bào)全媒體記者 吳宜芝 楊賢清 通訊員 龍劍英
吳慶華話少,平日里悶頭干活,話都攢著勁兒使在手上。
這個(gè)不到一米六的湘西漢子,被30多年巡路搶險(xiǎn)的日頭曬得黝黑精瘦,倒顯出山里人特有的結(jié)實(shí)身板。
平日里靦腆不搭腔,可一旦說(shuō)起公路養(yǎng)護(hù),眼角會(huì)亮晶晶地漾起波紋。
春末,雨霧漫上國(guó)道G319線,吉首市河溪鎮(zhèn)路段,熒光綠身影晃動(dòng)著。
身為吉首市公路建設(shè)養(yǎng)護(hù)中心干線公路養(yǎng)護(hù)股副股長(zhǎng)的吳慶華,早早帶著班組人員前來(lái)清理因邊坡垮塌而淤塞的邊溝。
撬棍別開(kāi)攔路石,鐵鍬鏟走黃泥漿,冷雨濕泥里,過(guò)路司機(jī)搖下車窗遞煙,他擺手婉拒,倒是看見(jiàn)清理干凈的邊溝時(shí),笑得眼尾皺成了車轍印。
“7點(diǎn)出工,活干完收工。累啥?本分嘛。”吳慶華是公路“老將”,器械、工具操作起來(lái)游刃有余,仿佛八磅錘、撬棍、鐵鏟等是從胳膊上長(zhǎng)出來(lái)的。
八磅錘上下?lián)]舞,錘頭不偏不倚正中大石,四散的裂紋如32年公路養(yǎng)護(hù)歲月織下的密網(wǎng)。
吳慶華是“路二代”,父親扛著道班旗走了大半輩子,他也跟著在砂石路上摸爬滾打長(zhǎng)大。
1993年,20歲的他接過(guò)父親的鐵鍬,走上了相似的路。這一走就是32年。
他記得父親在路上給他上的第一課:“甘當(dāng)路石,敢承大重”。因此盡管養(yǎng)護(hù)工作風(fēng)吹日曬、臟累孤獨(dú)。可每次出工,他總搶著干最臟最重的活,以膠鞋丈量四季。
2024年初,吉首市矮寨坡頭大雪紛飛。作為重要通道,矮寨盤山公路破冰除雪、保通保暢任務(wù)重、責(zé)任大。作為應(yīng)急處置搶險(xiǎn)人員,吳慶華承擔(dān)著徹夜反復(fù)操作機(jī)械設(shè)備保通保暢的重任。
“鏟雪一趟兩個(gè)小時(shí),雪大時(shí)隔一個(gè)小時(shí)就得啟動(dòng)一趟,太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臉,餓了就吃桶泡面墊墊。”他看似隨意地、滔滔不絕地鋪陳記憶里的細(xì)節(jié):烈日當(dāng)頭,水泥和著汗水修補(bǔ)路面;冰天雪地,用雙手撐開(kāi)一團(tuán)團(tuán)溫暖和安寧;狂風(fēng)暴雨,與時(shí)間和風(fēng)雨賽跑,保證道路通暢……
還有一次,吳慶華在巡查國(guó)道G352線K133+900m時(shí),發(fā)現(xiàn)涵溝積沙嚴(yán)重,排水幾乎失效。他立即組織班組進(jìn)行疏通作業(yè)。
眼看工具清理效果差,矮個(gè)子的他二話不說(shuō),一下鉆入涵洞,用手清理垃圾。經(jīng)過(guò)一個(gè)多小時(shí)的努力,水溝終于疏通。
除了將手中的事做好、腳下的路修好,吳慶華還愛(ài)“搗鼓”新設(shè)備,是名副其實(shí)的“設(shè)備通”。
每次單位來(lái)新“伙計(jì)”時(shí),他總搶著試,逮著廠家技術(shù)員問(wèn)東問(wèn)西,活脫脫小學(xué)生模樣。擦得锃亮的操作臺(tái)前,他也總是手把手地將半生經(jīng)驗(yàn)給后生們傾囊相授。
事實(shí)上,這些年,隨著全州公路路況改善,公路養(yǎng)護(hù)機(jī)械設(shè)備更新,不少同他一般年紀(jì)的養(yǎng)護(hù)人員慢慢退居幕后,而從“小吳”熬成“老吳”的吳慶華仍堅(jiān)持在公路一線。
問(wèn)他咋不退二線,他總笑呵呵摸摸頭。
“對(duì)公路有感情了,坐不住的,咱養(yǎng)路人的日子就該過(guò)在路上。”望著青翠山頭下奔流不息的春水,吳慶華笑臉盈盈。此刻,他平凡得像腳下的鋪路石,卻讓每段坦途都有了滾燙的筋骨。
記者手記:
在公路上,養(yǎng)路人“吳慶華”還有很多,他們沒(méi)有驚天動(dòng)地的故事,卻把三十年、四十年光陰熬成瀝青,融進(jìn)每一寸路基。
路,是他們的命根子;車,是他們的牽掛。千萬(wàn)塊沉默的“鋪路石”,托起的是千家萬(wàn)戶的團(tuán)圓路、致富路,他們把歲月碾進(jìn)柏油,將擔(dān)當(dāng)鋪成坦途。